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位于太原市迎泽区,是太原市的地标,是太原市最早的广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在一座老太原城城门的废墟上建起的。这座城门就是首义门。
2021年10月,历经70年风雨变迁的太原五一广场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改造,它是城市文脉的延续,体现着太原乃至山西的历史文化传承。
这座挺拔的建筑,是首义门仿古建筑,它是五一广场改造工程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太原打响了辛亥革命在黄河以北第一枪,是太原城市精神象征和城市灵魂,是文化太原、英雄太原的载体,也是太原城市的屋脊和坐标。
首义门是太原城的南东门,建于明洪武初年,当时叫太平门。太平门内的道路叫晋藩前大街,大街的北端是明代藩王、九大塞王中排位第一的晋王王府皇城的南门——南华门。第一代晋王朱棡就藩太原后,因皇帝的圣旨皆由太平门入城送进王府,于是将太平门改名为承恩门。同时将太原南城墙西边的城门名字由朝天门改为迎泽门。迎泽与承恩二字出自皇家祭天祭文“承迎恩泽”。
清代中叶来自东山的山洪顺东南城墙而下冲毁承恩门关城及箭楼,政府重新拨款修此门,自此后承恩门别称新南门。

不过承恩门长年封闭,直到1907年正太铁路竣工后,太原火车站建在承恩门外,这座封闭了数百年的城门才又重新打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山西支部立即响应,并积极筹划在太原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28日下午,同盟会员拟定军事计划,于10月29日发动起义,新军士兵冲入太原城后,攻占山西巡抚衙门,成立山西军政府。太原起义不久,山西很快就发生了大同起义和晋南光复,革命烽火遍及全省。由此,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宣告结束。
山西是黄河以北第一个起义的省份,其光复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山西起义消息传至北京后,朝野震动,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因而就为辛亥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1912年9月19日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山西大学堂各界千人欢迎大会上演讲时总结说:“……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先生盛赞山西响应南方起义,牵制清军南下的历史功绩,肯定了太原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因这里是辛亥革命太原首义发生地,为纪念太原辛亥义举,遂改新南门为“首义门”。
说到太原首义,必须说说清朝最后一任山西巡抚陆钟琦,关于陆钟琦的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革命刀下新旧社会交替的替死鬼,有人说他是革命者自证革命严肃性的劫数,还有人说他完全可以不用死。说法众多,似乎内情丰富。
陆钟琦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生人,祖籍浙江萧山,字申甫。
出生在清朝末期的陆钟琦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了进士,那年他也才四十一岁,可见陆钟琦也是有些才华在身上的。之后,陆钟琦做过溥仪父亲载沣的老师。
在清朝末年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像陆钟琦这样的人升官并不是一件难事。
1911年,63岁的陆钟琦从江苏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
巡抚是一个地方的军政大臣,掌握着该地的军政要务,相当于现在一个省的省长或者省委书记这种级别的官职。
封建社会里,读书人读孔孟之书,为的就是居庙堂之位。官位做到巡抚,放在历朝历代都算是成功了。
可惜,陆钟琦做官的时候是在清朝末年,清朝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面临崩塌。
1911年10月6日,陆钟琦走马上任,抵达山西太原。这位清朝最后一位山西巡抚,不知道在山西太原等待他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灭门之灾。
19世纪末,腐朽专制的清王朝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决定建立近代化的军队和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教育制度。1898年,山西武备学堂在太原应运而生,但仅仅一年之后就被山西巡抚毓贤裁撤。1902年夏天,重新设立的山西武备学堂向全省招生,第一期文化考试的题目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论。两年后,山西地方政府从这120名学员中选拔了24人留学日本,以便将他们培养成为用现代军事思想来保卫专制王朝的中、上级军事人才。临出国之前,有关官员专门教育他们不得与革命党人接触,然而,不论是后来加入了同盟会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马开崧,还是没有加入同盟会的姚以价、黄国梁等人,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并成为日后太原起义的领导力量,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四人,更是成为同盟会中仅有二十八位成员的秘密军事骨干组织“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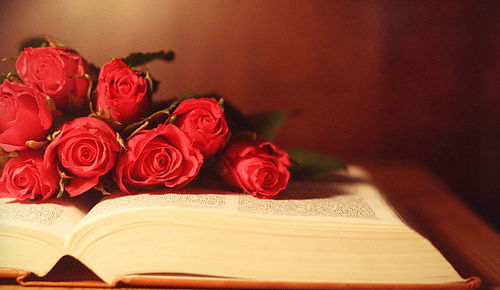
1909年,山西武备学堂第一批留日学生陆续回到太原,很快就取得了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按照同盟会“南响北应”的初步战略构想,山西同盟会开始为响应南方起义积极准备。当时的山西旧官僚中,山西巡抚丁宝铨素称能吏,他的主要助手夏学津管理军队极为严厉,同盟会决定扫除这两个革命的主要障碍。
早在两年前,山西各校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后,创办了山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晋阳公报》,这一舆论工具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夏学津的妻子姿容美艳,据说是拜认丁宝铨作了义父,时常出入巡抚衙门,与丁宝铨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此事被《晋阳公报》曝光之后,丁、夏二人声名狼藉。不久,夏学津奉命率领两营官兵协助文水、交城两县禁烟,在遭遇农民抵抗时处置不当,激化矛盾,以至酿成血案,四十余位农民被军队开枪打死。当时,这一惨案被《晋阳公报》披露,全国多家报社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夏学津等一批当事官员被革职,丁宝铨受到降职处分,调离山西,同盟会的“倒丁运动”获得成功。
丁宝铨去职后,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有孝子之誉的陆钟琦是光绪十五年进士,做过溥仪父亲载沣的老师,曾负责直隶赈灾事务,在湖南任上整顿司法,澄清积案,用封建社会的眼光看可以算得上一个比较称职的官员。虽然陆钟琦较之晚清那些腐朽的保守派还算开明,但仇视革命,极端顽固,当时剪发的男子已经很多,陆钟琦已经剪发的次子陆光熙每次见父亲却都要戴上一条假辫子。
10月6日,陆钟琦抵达太原,四天之后,也就是永载史册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江西先后响应,陆钟琦忧心忡忡,预感到革命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开始与他的下属们研究对策,采取预防措施。10月22日,邻省陕西爆发革命,宣布独立,对山西产生强烈的冲击,陆钟琦紧急下令平阳清军布置河防,预防陕西革命军进入山西。
就在这个时候,陆钟琦在北京任职的次子陆光熙突然来到太原,陆光熙为什么归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受其父之召回来商议对策,二是山西的中间派希望利用他来说服陆钟琦“和平让渡”以避免革命。
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留学国外的官宦子弟一样,曾留学日本的陆光熙并没有被一帆风顺的锦绣前程所羁绊,而是以一腔热血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同盟会。作为同学,陆光熙虽然与阎锡山没有深交,但他不仅知道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而且是山西革命的关键人物,因此,陆光熙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就拜会了阎锡山,从阎锡山和陆家后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而是一次秘密谈判,双方甚至初步达成了某种意向。
几乎所有的革命都难以避免激进的暴力和盲目的破坏,和平过渡,无疑是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将暴力与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一个途径。就在陆光熙为此积极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对阎锡山等同盟会同仁的身份始终都守口如瓶。陆光熙既没有因为自己的革命信念而抛却人伦,也没有为了父子亲情而背叛事业,然而,如此优秀的一个热血青年,他的建议却得不到父亲的采纳,自己也最终倒在了起义士兵的枪下永不瞑目,而他同盟会员的身份直到几十年后仍然有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阎锡山与陆光熙之间当时难免存在着猜疑与戒备,如果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运作,在山西实现和平过渡并非没有可能,但陆钟琦的顽固与愚忠却将这一希望化为泡影并促使山西革命提前爆发。
当时山西军队分为新军和旧军两部,驻扎于太原的山西新军正式成立于1909年12月,番号为暂编陆军第43协,协相当于现在的旅,共约4500余人,协统谭振德虽然是一个顽固分子,但并不直接掌握兵权。43协下辖两标,标相当于现在的团,第85标驻扎于城外狄村和岗上村一带,标统黄国梁,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一向同情革命,而且是阎锡山的结拜兄弟。85标下辖三营,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和第二营管带姚以价都是革命同情者,只有第三营管带熊国斌是顽固分子。第86标驻扎于城内后小河,标统为阎锡山,除了第三营管带瑞镛为满族人外,另外两个营的管带乔煦、张瑜均为同盟会会员。山西旧军共约四千余人,主要驻扎在全省各地,太原的旧军共有巡防马队、满洲城护卫旗和巡抚亲军卫队三支,共约六七百人,城内另有巡警约千人。
同盟会极为重视在新军中发展力量,从下级军官到基层士兵普遍支持革命,陆钟琦对此也有所察觉,当10月22日陕西发生革命之后,陆钟琦决定调用旧军回太原驻防,而将太原新军调往外地以分散革命力量。
10月25日,陆钟琦命令第85标在10月28日分批开赴蒲州。新军力量一旦被分解,将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并增加太原起义的难度。阎锡山立即召集同盟会主要成员在黄国梁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清政府为了防止军队革命,平时部队不装备子弹,只有在调防或临战前才能领到弹药,一旦领到弹药,也就意味着新军有发动起义的可能,同盟会决定等85标领到子弹后由85标先行发动起义。
按照陆钟琦的命令,黄国梁率领标本部和直属骑兵营在10月28日下午开拔,其他即将出发的各营也在当天领到了子弹。与此同时,同盟会员们向新军部分下级军员和基层士兵传达了起义指示,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在争取高级军官时,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已经回到城内寓所,督练官苗文华表示响应,考虑到曾留学日本的第二营管带姚以价向来同情革命,在军队中威望较高,同盟会员们将起义的计划通知了姚以价并推举他为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当仁不让,慨然允诺。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第85标第一营、第二营一千余名官兵在狄村军营誓师,姚以价声泪俱下地痛斥了清王朝的腐朽专制,并以民族主义激励士气,同时申明军纪布置了作战任务。誓师结束后,两营官兵向太原城进发,途经东岗村第三营军营时,部分事先得到通知的官兵加入了起义军。
拂晓时分,起义军赶到承恩门,埋伏于吊桥附近,不久,已被同盟会争取的巡缉队警官李成林打开城门,起义军趁着微露的曙光一拥而入,攻入太原。
按照既定计划,苗文华率领第一营攻打满族人聚居的满洲城,杨彭龄、张煌率领第二营攻打巡抚衙门,姚以价进驻东夹巷教会医院指挥,同时安抚外国人。
当第二营跑步冲到北司街口时,从满洲城方向已经传来了枪声,起义部队快速赶到巡抚衙门,用石条砸开大门,击毙门卫马八牛后冲入巡抚大院,从睡梦中惊醒的巡抚亲军卫队未做抵抗即四散逃逸。相形之下,一省长吏陆钟琦身上充满了旧式官僚的迂腐之气,面对蜂拥而入的起义士兵,他愤然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一片枪声响起,来太原仅二十三天的陆钟琦和他的仆役李升饮弹身亡,这时,身穿军服携带手枪的陆光熙怒斥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又一片枪声响起,同盟会成员陆光熙就这样倒在了革命同志的枪下。起义士兵冲入内室,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仆役万春先后被杀,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陆鼎元也被刺伤。
起义士兵从巡抚衙门出来后,协统谭振德闻声赶来,厉声问道:“你们是哪一营的,谁叫你们造反?!”起义士兵回答道:“我们是起义的革命军,你随不随?”谭振德怒道:“我不随!”说完扭头就走,起义士兵开枪将他击毙。事后,同盟会出于人格上的尊重,对陆钟琦父子与谭振德均予以礼葬。
当年清军攻入太原之后,为保证驻防清军和满族人的安全,在太原城中修筑了满洲城。满洲城在光绪年间被洪水冲圯,满人全部迁出,在今天的新城街一带另建新满洲城,原满洲城从此被称为旧满城,也就是今天的旧城街。起义军在满洲城遇到旗兵的顽强抵抗,一时难以攻取,炮兵营将火炮从承恩门拉上城墙,拖到小五台城墙处,居高临下向满洲城轰击,几声炮响之后,满洲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
当时太原的满洲人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虽然享受国家拨给的田产,但不事农桑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境遇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八旗子弟”那般逍遥纨绔。由于山西同盟会执行的是平等的民族政策,因而在革命期间并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出现过滥杀满人的现象。满洲城守尉增禧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后退出政界,在太原一中教授生物和美术。增禧早年擅长工笔画,后来因为视力原因而改画写意,1929年,冯玉祥将军暂居晋祠时,曾聘请他教授国画。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府希望增禧担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他坚辞不受,一名日本军官向他求画也被婉拒。增禧后来以行医为生,有人曾见到过他保存的傅山先生的医学著作。
从拂晓五时到清晨八时,随着巡抚衙门、满洲城以及弹药库、军装局、藩库等要害部门的攻取,效忠于清室的旧军溃散投降,太原起义宣告成功,清王朝在太原长达267年的统治就此结束。当天上午,阎锡山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推举为都督,从此开始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统治。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八,阎锡山28岁的生日。
推翻清政府的太原城内一片新气象,革命新军,社会帮派,官司府学堂,一副改头换面的气象。这时候的太原,从大局上来说还算稳定,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依然暗流涌动。
虽然推选出了阎锡山担任山西军政都督,但是他并没有让所有人信服。
军队方面,除了革命新军之外,以晋南李鸣凤为代表的民军依然势力强大,阎锡山拥有一个名头,却没有实际掌权。
政府方面,新旧交替之时,涌现出大量的人参加革命,这其中有真心实意追随革命的人,也有在其中观察社会风向变化、滥竽充数的墙头草。
新政府内的人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党派,不同阶层,实在无法做到齐心协力,和衷共济。
新政府无法做到团结统一,袁世凯一方又虎视眈眈。
针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对同盟会华北地区负责人张继说:“内部先统一,然后同心努力革命,现在既然公认阎锡山为都督,就应该支持他,倘若内部再发生事故,岂不是给袁氏可乘之机。”
后来,孙中山来到太原,一再强调团结的事情。孙中山在太原“苦口婆心”的团结演讲起到了作用,太原各界都大为震撼。
1912年年底,河东民军解散,山西军政府都督阎锡山开始逐渐掌权。政府内部的各种重要职位也都有同盟会的会员担任,山西这片地方开始慢慢统一起来。
太原起义虽然历时较短,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时间上说,山西在全国是继湖南、江西、陕西之后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并与陕西连成了一片。从地理上说,山西近在天子脚下,随时有可能兵出娘子关、大同而断绝南北交通、直趋北京。从影响上说,太原起义不仅带动和促进了山西全省的光复,而且,这场在清政府自以为统治最为稳固的北方爆发的起义,对腐朽的清王朝而言,将是巨大的震撼和威胁。
革命爆发,有人欢喜有人愁。刚刚上任五天的山西巡抚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陆钟琦看来,自己的官位刚刚到手,大好前程才刚刚展开,若是革命成功,官位不保不说,就连性命都不一定能保住。
在革命还没在太原爆发之时,陆钟琦开始了他的准备。忧心忡忡的陆钟琦加紧山西省内的排兵布置,他加紧河防布置。
因为,革命新军已经在西安起义成功,陕西的旧政府已经被推翻。陕西与山西之间只有一河之隔,革命新军随时有可能冲入山西,打响起义的第一枪。
陆钟琦加强河防布控,一方面,防止陕西的革命军进入山西。另一方面,河防布控的加紧能够把太原城内受到革命影响的新军,调出太原到河东去堵截陕西起义军可能的东渡。
陆钟琦这样的做法可谓是一箭双雕。只可惜,陆钟琦的意图被阎锡山等新军头目给识破了。
陆钟琦的儿子陆光熙,在山西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来到了父亲身边。陆光熙曾经在日本留学。他和革命新军里的重要人物——阎锡山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
特殊的身份,敏感的时机,陆钟琦将儿子陆光熙喊到身边的做法无法不引人关注。
“在山西巡抚陆钟琦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做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之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
这是阎锡山在台湾《早年回忆录》中写的话,可见阎锡山与陆光熙虽然是同学,但是两人之间的交情不仅不深,甚至有些避之不及的感觉。
陆光熙来到陆钟琦身边之后,就立刻与阎锡山见了面。父亲陆钟琦坚决反对革命,但是他不一样。
作为去日本留过学的人,陆光熙看清了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在心里清楚,革命已经是一件无法阻挡的事情了。
不久之前,湖南和陕西的起义成功更是让陆光熙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这次来到父亲陆钟琦的身边是想担任一个调节的角色。
陆光熙很清楚,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坚决反对革命的清朝末代官员,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加入革命的,反对革命最后的结果已经很显而易见了。
又不想加入革命浪潮,又想在革命的大形势之下享受和原来差不多的安逸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折中。
陆光熙打算等到革命军打到山西的时候,自己出面,调停中立,争取到一个既不需要两方兵刃相见,又不需要陆钟琦投降的局面。
美其名曰“缓和革命,争取和平。”陆光熙计划得很理想,于是就有了他去找阎锡山谈话的场面。
“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
面对突然出现的陆光熙,阎锡山并不准备相信他。
阎锡山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或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
陆光熙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
陆光熙的话看上去充满诚意,但是阎锡山并不相信这位公子,他只是笑了笑,说了一句客气十足又模棱两可的话,“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你来我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
陆光熙和阎锡山的见面最终以两人各怀心事结束。
阎锡山处处警觉,不相信陆光熙说的任何一句话。他觉得,陆光熙的突然来访,完全是想要敷衍住他,为其父亲陆钟琦做掩护,让他完成运枪和开兵两件事。
陆光熙离开之后,阎锡山召集了其他革命党人,与他们共同商量讨论陆光熙来与自己谈话的事情。
众人经过商量之后,都觉得陆光熙来找阎锡山谈话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商议求同,实际上是在给他的父亲陆钟琦做掩护,“顶好也是敷衍出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拥戴上他的父亲,联合上大家做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
于是阎锡山与革命党众人没有把陆光熙说的话放在心上,依然制定了起义计划。
就在陆钟琦的儿子陆光熙和阎锡山谈话,想要调停中立,缓和革命的时候,陆钟琦自己做了一个加速自己死亡的事情。
他下令将山西的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中的三千支连带着子弹一起借给河南。与此同时,陆钟琦又加快了调兵的步伐。
陆钟琦这样的举措让阎锡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陆光熙的劝说全部幻化为泡影。
坚定了自己猜测的阎锡山开始有了紧迫感,他觉得山西起义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陆光熙也在劝说陆钟琦,他希望父亲能够认清局势,不要再固执抵抗。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起义俨然成了定局,无法撼动。陆光熙劝陆钟琦能够和自己一样,等革命军来山西的时候,不要抵抗而是和革命军合作,求取共赢。
陆光熙的一番劝说彻底惹恼了陆钟琦,他对自己精心培养出来的儿子破口大骂:“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
陆钟琦这种被封建思想完全浸透的人,誓死要做大清王朝的孝子忠臣,誓死也要报答朝廷,绝不可能违逆朝廷。
阎锡山固然是没有相信陆光熙说的话,但是陆光熙找他谈话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阎锡山等人依然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确定了具体的起义时间。但是在真正起义之前,阎锡山又告知一、二两标,如果抓住陆钟琦和陆光熙,只是囚禁起来,不要真的伤害到他们。
陆钟琦精心布下的防控很快就被来势汹汹的革命新军给突破了,清朝政府在山西彻底地倒下了。
1911年10月29日凌晨,革命新军攻占太原城,按照阎锡山事先吩咐的那样,革命新军并没有为难陆钟琦和陆光熙父子。
阎锡山在巡抚衙门做好准备,他让陆光熙把陆钟琦叫来,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陆钟琦不急不缓地从他的居所东花园来到了巡抚衙门的议事厅。阎锡山问:“我等已经准备参加辛亥革命,不知你参不参加?”
陆钟琦一听阎锡山问出这样的话,不禁怒从心来,自己身为大清朝廷命官,怎么能够与“逆臣贼子”同流合污,背叛大清呢?
陆钟琦整了整自己的衣冠,厉声说道:“我不参加!”
站在一旁的陆光熙此时十分焦急,父亲这般厉声拒绝,自己之前一番苦心白费事小,眼下性命都难以保证。万一惹怒了眼前的革命新军,很难不保证他们会开枪杀了父亲。
陆光熙连忙说道:“你们不要开枪,我们可以商量。”
可是,陆钟琦却对儿子的打算视若无睹,他依然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
陆钟琦话音刚落,阎锡山就举起手中的枪。只听见一声枪响,陆钟琦一头倒地,没了气息。最后一任山西巡抚就此消失。
陆光熙见父亲死在枪下,心中悲痛万分。之前做的种种打算全部白费,到头来还是没能够劝住父亲。
陆钟琦和陆光熙父子二人虽然理念不合,但是感情却很深厚。陆光熙见父亲已死,也没了活下去的希望,就对阎锡山说:“把我也打死吧。”
阎锡山虽然对陆光熙一直保持警觉和戒心,但是毕竟同学一场,也不忍心亲手打死陆光熙,就叫身边的士兵开枪。
因为当时局面混乱,所以关于陆钟琦和陆光熙的死还存在一些小小的争议。
有人说是阎锡山开枪打死了陆钟琦。可是在阎锡山自己的《早年回忆录》中却并没有承认是自己开枪击毙了陆钟琦,而是说是陆钟琦先开的枪,引起了革命军士兵开枪,陆钟琦最后死于混乱之中。
“当时因陆巡抚之随侍者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死于枪乱之中。”
阎锡山虽然和陆钟琦立场不同,却也被陆钟琦最后那一份忠勇孝精神所打动。
“他们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立场是个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陆钟琦的死不仅仅是因为新旧交替之际他代表的是旧派势力,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已经被封建社会“忠君事主”的思想完完全全禁锢住了。
一直到陆光熙劝他的时候,他都觉得,朝廷对他有知遇之恩,自己为朝廷献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被封建思想禁锢住了,所以陆钟琦只看到了朝廷对他的知遇之恩,完全没有看到清政府的腐朽懦弱,软弱黑暗。
阅读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