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野外,视野豁然开朗,天空辽阔高远,大团大团的白云在天上游走,道路两旁林木葱翠,远山若隐若现。
此刻的正果镇,正在蓝天下等我,山不高,路途却不近。车子行驶了一个多小时,道路旁突然出现一条清澈的河流,这就是增江。
增江是增城的母亲河,相对于长江黄河,她更像一个乖巧的小媳妇。河水从新丰县山里流出来,穿增城而过,蜿蜒汇入永汉河。对于正果,我更愿意把增江水看作过客,它日夜奔流,穿过正果,从不回头。
我愿意跟着她奔跑,跟着她走进正果。
正果像一个深藏闺阁的女子,在深山里独自守着属于她的安静、与世无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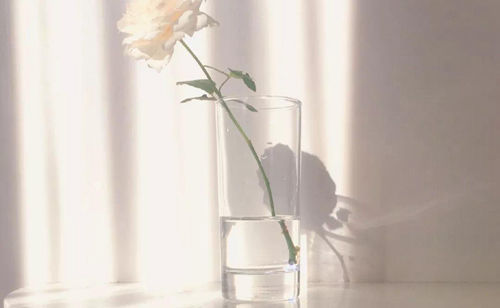
但她并非与世隔绝,从地图上看,她犹如一颗朴实的木雕珠子。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像一条绳子,把正果穿在正中间。山路一端是山水城市惠州,另一端是繁华的广州。而我就身居广州市区。有了这条山路相连,我常常会想起正果,想起那里的山风、森林,想起那满山的琵琶、荔枝。
间或在夜晚,我在家里端起酒杯,酒香是仿佛从正果镇上众多的酒坊里飘来的。此时,我会傻傻地伸出手,想抖一抖穿在我和正果之间的这条绳子,和她共享美酒,共度良宵。她若感知到我的心思,满天的星光会眨眼睛,窗外的风儿会卷起落叶……
每一次去正果,我都是沿着这条河流进山。河流两边有很多森林,是广州的天然肺叶,除了风景优美的自然风光,富氧的空气是我奢侈的享受。不必开空调,不必扇扇子,只需打开车窗,闭上眼睛,尽情呼吸山里的空气。山林不会怪罪我的贪婪,我也不会浪费它的馈赠。进入正果镇,拐进一条小路,只需几分钟,就到了圭湖村的朱叔家。
六月,正是荔枝成熟时节,而增城正果的荔枝最负盛名。在盛果期进入远近闻名的优质荔枝产区,我有点忘乎所以,对每一棵荔枝树,都想大发感慨。
荔枝,这个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开始种植的热带水果,最早起源于云南,但是经过数千年后,只在南方诸地保留了下来,而增城则是最为重要的优质产区。这是大自然进化的结果,也是增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致。
正果的山,不陡不峭,风化层松软丰厚,给荔枝和人类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山林掩映下,或密或疏地坐落着几栋民居。绕于民居间的,是鸟叫,蝉鸣,和咕咕的流水声。
朱叔的家建在村中的高地上,一座传统岭南小院,房子极具乡村风格,但又不老旧陈腐。院子里有几棵荔枝树,树上,还挂着一些鲜红的荔枝,树下是光洁的石凳。在村子里,土狗是少不了的,朱叔家养了两条狗,一条懒洋洋地躺在石凳下,另一条摇晃着尾巴欢迎我们。
我们在石凳上坐下,朱叔忙着给我们沏茶,桌上已经摆上了带着绿叶的荔枝。我知道,好客的朱叔期待着与我们分享荔枝,我迫不及待地剥开果皮,把晶莹洁白的果肉放进嘴里,清甜的味道刹时在口腔弥漫开来,一直甜到心里。如此新鲜美味的荔枝,让人停不下来,吃一颗荔枝,品一口红茶。茶水的微涩与荔枝的甘甜互相中和,相得益彰。
在城市的高楼小区,见惯了邻居互不往来,看到朱叔的邻居在树上摘荔枝,顿觉温馨。邻家的人爬上高高的老荔枝树,直接跨在树叉摘果。树梢摘不到的地方,就用特制的长竹竿。竿头绑了一把弯刀,一条活动长绳连接着竹竿两端。只要看准了枝头的荔枝,用左手握紧竹竿,把弯刀对准树枝,右手用力一拉,弯刀准确地把带着荔枝的枝条剪了下来。因为有枝叶的支撑和减压,荔枝一般不会摔坏。但若是碰到枝叶不多的,就要两个人配合了,一个人依旧用带弯刀的长杆对准荔枝的细枝,另一人就用一个带网罩的长杆,用网罩罩住荔枝,待细枝断了,荔枝就完好无缺地落在网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正果人常年在山里生活,只能从山里挖掘财富,为了一日三餐,为了挣钱盖房子、买车子、子女读书,他们在跟大山和果树打交道过程中训练出了属于自己的本领。看似简单的工具里,浓缩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假如他们过着条件优越的的生活,不需要苦思冥想,也许他们发明不出这些充满智慧的生活良方。
一直以来,世间流行的心态是向往锦衣玉食,豪宅良境,追求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进城,城镇化建设等名词一直是生活进步的代名词。有些人嘴上说不追求,或许只是自身条件无法获取,若要有足够的能力,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追求宽敞漂亮的豪宅。
曾经,朱叔也不例外,他年轻时从正果走出去,进城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终有所成。
但是,一生奔波之后,朱叔心底对家乡的原生态生活的怀念又鲜活起来。退休后,他毅然回到正果,过起了乡村生活。种菜、养鸡,养鸭,还养了山羊,生活基本自给自足,还找回了珍贵的健康和快乐。
院子里的柴火灶,简单而又干净,灶膛里柴火正旺,映红了朱叔的脸。
他用几个不锈钢碗放了适量的米和水,放在大铁锅中的架子上,准备做蒸饭给我们吃。闲谈中,他又斩好了鸡和鸭,调好了味道,也放在大锅里蒸。
房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在荔枝树上空盘旋,给山居平添了几分诗意。

炉灶旁,一个饱经沧桑的石臼,被朱叔用来盛水。石臼有些年份了,从被磨得光滑的内壁,可以看出它饱受捶打的一生。如今,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没有人用它来舂米,但它和朱叔一样,在山里依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快乐,不会寂寞,也不会被生活淘汰。
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桌,自养的鸡鸭和自种的菜心都有着食物原本的味道,甫一入口,久违的乡村味觉顿时涌上来,恍如回到旧时光。
午饭后,他们各自回屋午休。我无午休习惯,加上吃得太饱,便一个人出去走走,顺便消食。
坡下就是万里碧道,和增江相依相偎。碧道两边都栽种着绿竹,阳光洒下来,竹影斑驳,散落在红土的地面上,别有意境。虽是正午,在竹林的遮蔽下也不觉热,一个人独行于绿道上,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的。明媚的阳光投在竹叶上,竹叶在阳光下舞蹈,一阵风吹来,他们发出簌簌簌的声响,给宁静的中午增添了些许热闹。
在路边,不时看到一些菜地,地边儿上的白色野菊花散发出清幽的香味,引来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几只不知疲惫的鸟儿在树上鸣叫,令山野更加空旷。鸟鸣林更幽,陌生的地方令我有点胆怯,我不时回头,看看有无人过来。这个时候,人是没有的,只有几株枝干虬劲的老乌榄树,如一个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我这个外来者。
大树的背后,出现一条小径,弯弯曲曲通往增江河。顺路走下去,草地上的野苋菜长得半人高,顶上还举着一穗穗种子,毛绒绒的穗子令我突然想起北方的谷穗,想起狸猫的尾巴。走过一片浅滩,滩上水草丰茂,迎风摇曳。浅滩延展之处,清澈透明的河面便出现在眼前。不远处,有两个人在垂钓,给河岸平添几分人气。
我在河边的石块上坐下,凝望着对面青绿色的山岚。那里,有朱叔承包的几十亩荔枝林。因为天气炎热,山里天气又多变,出于安全考虑,朱叔没有安排我们去山上采摘荔枝,而是叫人一早摘回来,等着我们品尝。
果然,刚才还好端端的艳阳天,突然山风袭来,乌云遮天盖日地压过来,很快覆盖了半个天空。不远处隐隐有雷声响起,西边的天空还出现了闪电。眼看着暴风雨就要来临,我忙起身往回走。
走到半路,乌云渐渐西去,雨最终没有下来。也许,是山坡的地势改变了气流,令风雨改变了方向,又掉头去其它地方了。我们面对的黑暗,不一定都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出于生存和安全本能所致,躲避和预防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回到朱叔门口,传来一阵悦耳动听的乐声。曲目很熟,是经典的粤剧曲目在。院子里,朱叔弹中阮、黎所拉高胡,英姐弹扬琴,配合得如行云流水,粤韵十足。
朱叔以前曾任增城粤剧团的团长,也是风云人物,退休后又加入了业余曲艺社,经常和一帮爱好曲艺的人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极尽雅兴。
他们沉浸在弹奏中,我则沉醉于他们的乐曲中。我深知,除了丰衣足食,任何时候,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这简朴无华的山居生活中,音乐成了不可或缺的娱乐。
金姨在石凳上修剪荔枝的枝叶,羊圈中的黑山羊一直咩咩地叫着。朱叔把它们放出来,三只羊径直跑到石桌边,吃簸箕里的荔枝。领头的山羊不怕人,用舌头卷起一颗颗荔枝,拼命地往嘴里送,它歪着头,吃得欢快,调皮捣蛋的神情惹得我们忍俊不禁。
金姨把荔枝移开,它们又吃起地上的荔枝叶来,过一会又去吃地上盆里的米饭,好像饿坏了,恨不得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进肚里。山羊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了食物,似乎没有更多能够诱惑到它们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烦恼。
朱叔穿着粉红T恤,脸庞红润,气色很好,性格乐观开朗,和蔼可亲,说话时眼睛里满是微笑。他在院子里忙碌着,山羊跟在他后面转圈,大白狗也站在石凳上,垂着长长的紫色舌头,看着山羊和朱叔。
荔枝堆满了屋子内外,我们的手和嘴几乎没停过,随手抓起几颗荔枝,剥了皮就送进了嘴里。面对如此新鲜美味的荔枝,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它们的诱惑。古人也不例外,苏东坡寓惠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虽有文学夸张成分,但荔枝的诱人程度可见一斑。
岭南是好地方,并非虚传,气候条件好,水果也就丰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不同的新鲜水果。但荔枝这种鲜果,有自己的脾性,虽然历史上再四川涪陵、云南等地有过足迹,经过多年进化,现在只有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带才能生长。
我对苏轼的诗句虽早有耳闻,但一直不知荔枝为何物,还是早年到增城工作后,才真正接触到荔枝,第一次品尝荔枝。那时,觉得荔枝是人世间最美味的仙果。
后来,在广州成家后,虽然在街上也能买到荔枝,但总感觉不如增城现摘的荔枝好吃,似乎少了点什么似的。
今天,在朱叔家,在荔枝树下,我又吃到了当年的味道。或许,万物都有生存的环境,在特定的环境里,它的特性才能够发挥得最好。朱叔家的荔枝,因为吸取了当地山水的灵气,被大山和溪水赋予了魂灵,加上在山里新鲜空气里品尝,它得味道的确非城市里保鲜品可比。
爱屋及乌,因了人,对这里的荔枝喜爱有加。因了荔枝的鲜美,对朱叔他们也更加多了一份情感。和他们坐在一起,如家人一般,没有任何违和疏离感。
当年,他们曾把我当成家人,逢年过节和节假日,邀我去他们家,感受家庭的温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有几年没联系。但相识已久和信任的人,感情并不会因为时空的隔离而疏远。再次相聚,还是像过去一样亲切、温馨,无所不谈。他们的增城话,勾起了我内心久违的记忆。时隔多年,他们的话语依然是那么亲切悦耳,一个个特殊的音符和字音渗进了我的神经细胞,虽不会讲粤语,我也能听懂八九成了。
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漫长,在短暂的生命里,难免会经历出走,流动。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背井离乡似乎是最好的前进。曾经一次次告诉自己,对家乡的暂时别离,是为了更好的荣归故里,建设更好的家园。但是,渐渐地发现,总有一天,家乡会变成回不去的故乡。而自己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成了自己安放乡愁的地方。
我曾在增城生活了几年,喝了几年的增江水,吃了几年的增城米。几年的时间,足以让我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几年的时间,足以暂时安放我的灵魂和肉体。增城不像鄱阳湖那样,有我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亲情和乡愁,它只是我几年的栖息地,但是,我把人生最美好的几年时间留在了增城是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陪我度过人生最重要的几年。
所谓家乡,除了家族亲情,还有长年朝夕与共积累下来的快乐、安全感、和心灵安慰。增城,曾经与我分享喜悦,为我分担忧愁、思亲、乡愁。在我孤独时,是这里的山水和朱叔他们给我慰籍,让漂泊的我找到了心灵上的安全感。
在心中,这片充满灵气的山水,早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阅读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