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的时候,江老师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宣布了一个决定。
江老师说:我要开个书店。
说是全家人,无非是江老师的老伴儿、江老师的儿子和儿媳,江老师的孙女上小学一年级,学校组织去了夏令营,不在家。
决定当然不是才做出的,江老师说:我想了半年,想好了,开个小书店。
江老师口气轻松,但表情严肃,不像是玩笑。全家人的反应不大一样,老伴儿挺平静,看了一眼江老师,仍顾自埋头吃饭。儿子好像吓了一跳,放下筷子盯着父亲,儿媳也像是惊了一下,本能地看了看每个人的脸色,也停了筷子。

江老师的老伴儿把鱼头夹给江老师,用筷子敲了下盘子边说: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嘛。你看孩子们难得回来一趟,好好吃顿饭。
江老师的儿子问:老爸,你来真的?
儿媳嗔怪儿子说:让爸先吃饭,听妈的。
江老师说:那就先吃饭,吃过饭再说。
吃过晚饭,婆婆和儿媳抢着把碗刷了,收拾了厨房,泡了一壶不会影响睡眠的淡普洱,全家人便在客厅里的茶几旁坐了,接着说事。
江老师是名牌大学的教授,教历史的,主讲中国宋代史,自己的研究主攻方向是欧洲史。他自己写的书也快占了书柜里一个格子了。他不愿人们叫他教授,更愿意人们叫他老师。他觉得老师是最好的称呼,听上去既舒服又亲切,还平易,与人没有距离。还有一层,他觉得教授的称呼近于神圣,不是随便叫的。虽然他在这个岗位上,但他却觉得有些当不起,书读得越多,越觉得当不起。他摇着头说:罢了,现在教授太多了,其实我们这些人,哪里好意思称教授?他也不怕人们说他矫情,他就是愿意人们叫他江老师。
愿意归愿意,可是身边的朋友和同事,还是叫他教授的多,倒是学生们,喊他老师的多些。曾经有一年的研究生,也不知谁起的头,管他叫起了先生。他心里有些感动,更觉得当不起。旧时候,私塾的老师也叫先生,但他知道,这先生不是那先生,学生们叫的这声先生,已不单是老师的意思了。他跟学生说:先生是不能随便叫的,现在哪里还有先生?叫我是叫不得的。所以,还是叫我老师吧。
江老师从大学毕业就开始买书,那时候收入少,但是书也便宜,先是三本五本,十本八本,从伙食费里面挤钱。再后来,虽然是工资也慢慢涨了,但是成了家,有了孩子,书也慢慢贵了起来,日子还真是紧巴了一阵儿。还是买,买不了多就少买,买书是一直没停下。自己住的城市,大大小小的书店早跑遍了,出差去过的城市,也总要抽空儿跑上一两家书店。大半生下来,搬了四次家,房子一次比一次大,每次都是家里最大的那间做书房,老伴儿一向支持他,帮他把书房收拾得整洁明亮。老伴儿说:买书是零攒,买不穷日子,可是,人却慢慢富了。江老师听了老伴儿这话,心里惊了一下,惊的是,做了一生会计的老伴儿,除了几本财务方面的书,没读过别的,但却说得出这样的话,真是令他刮目相看。
现在的房子,已经是一百六十多平方米,最大的那间书房,三十多平方米,三面墙的书柜,从地到顶,满的。备了个小三角梯子,为着去够那上几层书的。围着写字桌的一圈,上下两边,也堆着书,窗台上也是书,阳台上也立了个竹子的书架,那书架跟了他大半生,舍不得扔的,还用着。这还不是全部,江老师的卧室里、床头柜上、床头格架上、床脚的衣榻上,都堆着书。
江老师年轻的时候,也不知自己有多少书,只要是有用的、喜欢的、又买得起的,就买。他不是个藏书家,不似藏书家那么讲究,什么版本啊,年代啊,套集齐不齐啊,他都不讲究,他只做学问,买书只为用着方便,若不是必要,他不大愿意去图书馆,他喜欢一个人关在书房里的感觉。
他五十五岁生日那天,儿子好信儿,给他大致数了一下,是八千多不到九千册的样子。儿子开玩笑说:老爸,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这书还不够万卷呢。江老师说:行万里路还罢了,可是读万卷书那只是古人的理想,是说要多读书的意思,其实古人哪里有那么多书?百卷书就得拉几马车。儿子说:老爸,您再加把劲儿,万卷书没问题呀。江老师说:买书不为数量,只为用。再说如今的书虽是出得多,但也是良莠混杂,要挑着买的。若只为数量,那有钱人,可以买个图书馆的,可他自己未见得读了几本书。儿子点头道:现在交通发达了,行万里路早不是问题,可是,读万卷书——
江老师说:读万卷书,的确不是件易事,另外读书也有方法,有工具书,常翻常用的,有买来大致过一遍就先放下的,有粗读的,有细读的,也有精读或是叫研读的。先别说细读,就说粗读吧,你算一下,一生读得了万卷吗?读不了。就算在你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不涉猎其他,你也读不了万卷。所以,古人说的读书万卷,到底只是理想,是个激励的意思。
那次与儿子谈话之后,江老师倒是冒出个想法,何不真的凑上万卷?想想又摇头笑了,人眼见着就老了,怎么幼稚起来?读书人不是藏书人,读书人攒书,是顺其自然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多起来的。还一层,买书要看用不用,有的人,他就算真买了万卷书,可里面若是有四五成不用的,或者他根本连一页都不翻的,那就打了折扣。江老师买书是严选的,所以,他的书都是可留的。纵是这样,他还是在儿子给数过了之后,整理出了两百多本,处理了。虽有不舍,但书房实在是放不下了。说处理,是都送了别人,江老师从不卖旧书的,他认为一本书,不论到了谁的手里,都是有用的,比化了纸浆有价值。
江老师在那一年就明白了,万卷书,说着容易,其实呢,单就钱这一项,对一个挣工资的人来说,就是个难事。就说他自己,儿子没给他数之前,他本以为这一屋子书,早过万卷了吧,数过了才知道,还差着一千多本呢。
如今,十年过去,江老师已是过了六十六岁生日,奔着七十了。这十年,是江老师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又连着出了两部著作。书呢,自那次儿子给数过了后,说是少买少买,但也早是过了万卷了。这几年又多了些托海外的朋友买的原版书,也有托港台朋友买来的书。六十岁生日那天,儿子又给数了一下,大约是一万三千本。六十五岁生日那天,再数,已是超过一万六千了。书房里早就放不下,又占了半个客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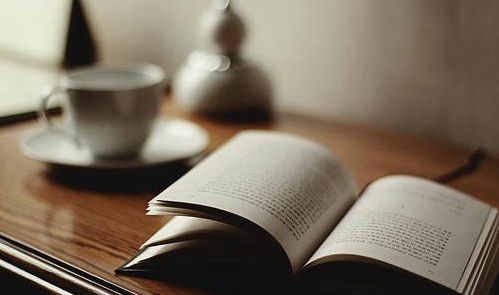
那天儿子拉着媳妇帮忙数过书后,兴奋地比画着说:老爸,把这大客厅改成书房吧,放两万本书没问题。
江老师摇头说:不能再买了,就这,还有些没细读呢,到八十岁也读不完。人的精力有限,可是学问是无限的。我也老了。
儿媳说:这些书是咱家最好的财富,可惜呀,我和晓凡都不是学您这行的。
江老师说:现在网上不是有个金句嘛,说是“风吹哪页读哪页”。说的是书读到了差不多的年纪,一个读书的状态。话说得挺诗意,也挺潇洒,可是呢,我觉得还是轻飘了一点儿吧。我做不到。要读,就好好读。我虽打算到了七十就不写了,但书还是要好好读的。所以呢,你们年轻,更得努力,虽是电子阅读方便了,但在你们各自的领域,还是要备一点儿必要的好书。
茶泡好了,客厅里飘着茶香。老伴儿知道是要接着刚才的话茬说事,就把电视调成了无声,又把每人的茶倒好了,自己端了一杯,慢慢喝着,看电视上无声的肥皂剧。
儿子说:老爸,您是什么诉求?是要投资个书店呢,还是要自己经营呢?
江老师笑着轻斥儿子:诉什么求,学两个新词儿,用得却不准确。先不说这个,先说书。儿子和儿媳都是一脸疑惑。江老师说:晓凡和小雪,你们俩在我这都没有书的是吧?你们自己的书都在自己手里是吧?
晓凡是儿子的名字,小雪是儿媳的名字。晓凡学的是电力,现在是电力公司的技术员,还没做到工程师。小雪是学医的,现在是主治医师,还没做到副教授。两人的性格却不一样,晓凡是那种出了大学门就基本不再读书的,靠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撑着,仗着脑子聪明,到急用了,临时抓过两本书翻翻,应付过去。如今这样的年轻人,也是一大把。小雪不同,毕业后又读了研究生,工作后也坚持读书。也是她的职业特点吧,学医的,三天不读书,还能装个样子,一个月不读书,说话就没了底气,半年不读书,便是个庸医,一年不读书,人就废了,还当什么医生?
小两口儿也有一个不小的书柜,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小雪的医学书占了大半,晓凡的书有一小半,这一小半里,还有些是武侠,不是他的专业书。
江老师喝了口茶说:原来晓凡有几本书在我的书柜里,你们结了婚后,都拿走了。小雪的书,我这是没有的,我又不懂医学。儿子着急地问:所以呢?江老师说:所以,我的这一万多本书,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做决定。晓凡问:老爸,您是说,要拿您自己的这些书,开书店?江老师点头道:正是。
晓凡愣了一下,又与小雪对视了一下,笑了,小雪却严肃着说:笑什么!晓凡说:我笑是因为老爸也学会幽默了。小雪说:爸是认真的。又转问江老师:爸,您是说,要把您一生攒的这些书卖掉?江老师又点头道:先别说卖不卖吧,主要是,有人读。小雪急了说:爸,不可以。您这是怎么啦?
江老师笑着说:小雪,你曾经说过,这些书是咱家的财富,又说,可惜你俩都用不上。我也想过这个事,若你俩是学文科的,那我自然留给你们,日后我作古了,怎么处理随你们的意。可是呢,你们又用不上,读来消遣吧,你们也没那个时间。所以,我就想开这个书店,因为书放在家里不用,就不是资源,有人读,才是。
晓凡转对母亲说:妈,您这两天没跟我爸吵架吧?江老师老伴儿眼睛盯着电视说: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跟他吵过架?晓凡问:爸,那您受了什么刺激?江老师说:晓凡,你认真点,我说了是来真的。或者换个说法,不叫书店,叫书屋也可。
晓凡这时才收了笑容,神色也紧张起来,他对母亲说:妈,你来一下,跟您说句话。江老师老伴儿说:我这正看着剧呢。晓凡说:电视剧又不是电影,断一会儿没关系,快来,小雪你先跟爸说着啊。
母子俩进了书房,晓凡虚掩上门,问母亲:妈,你俩最近检查身体了吗?老爸他身体有什么毛病吗?江老师老伴儿笑了说:难得你还有这份孝心,不是春节后才查的吗?不到半年呢。结果你不是也都看了。晓凡说:对呀,没事啊。那怎么着呢?江老师老伴儿问:什么怎么着?晓凡说:这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除了身体有什么不好的病,啊呸呸!他怎么会想到把他最爱的攒了一辈子的书卖了呢?江老师老伴儿用手里拿着的痒痒挠啪的打了儿子一下道:瞎说!你爸他身体好着呐。他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看不了那么多书了,他要卖就让他卖呗,你管他?
晓凡摇着头说:说不通啊。
两人出了书房,又回到客厅,小雪对晓凡说:爸说,不是卖书,是书屋,就像,像阅览室吧?或者叫读吧。是不是爸?江老师点头说:是那个意思吧。
晓凡问:借阅?收费还是不收费?江老师说:你怎么老是惦着钱呢,收怎么样,不收又怎么样?晓凡说:收,就是开图书馆,有偿阅览室,那一堆麻烦事呢,因为那叫经营。不收呢,白看。爸,你开慈善?
江老师说:白看又怎么样?书不就是给人看的吗?晓凡说:是给人看的。可这是您的私有财产。江老师说:换个词儿,不是财产,是资源,什么资源?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是这儿的资源。我这小两万本书,跟图书馆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但说起来也是个不小的资源,现在不都讲资源共享的嘛,那就不分你的我的。晓凡又做出哭笑不得的样子:老爸,哎,共享不是这么个共享啊。小雪轻打了晓凡一下说:严肃点儿,我看爸说的有点意思。还真就是书这个资源能共享呢,好比衣服,穿过了就不能给人了,好比杯子,用过了也就不能给人了。可是书却能重复给好多人看。江老师点头道:说的是。小雪懂我。晓凡抚着胳膊说:我这会儿挨了两下打了。明白了,您就是要开个免费阅读的阅览室呗。
江老师认真地点头道:正是。名字我也想好了,在学校的时候,我给学生们组织过一个书社,名字叫灯火,这个书屋,也就叫“灯火”吧。
晓凡说:名字不错,可是有个问题呀,老爸,现在科技发达,都看电子书了,手机阅读、电脑阅读,还有听书,看都不看,听着。纸质书越来越没人看了,以后书店和图书馆都没了,谁会来你的书屋?
江老师摇着头说:那都不叫读书。再说,你说得也过于绝对了。看着吧,会有人来的。
晓凡说:我怕您白忙活,我反对。江老师说:反对无效。小雪说:我支持。晓凡说:支持无效。江老师和小雪都瞪着晓凡。晓凡说:我是说,爸的书,辛苦攒了一辈子,是您的心爱之物,这一下子拿出去,让别人看?
江老师说:攒书不辛苦。再说,我不是为攒书,只为读,读过了,我这一生也快走到头了,再留就没用了。晓凡你学电力的,我的书你用不上,小雪学医的,也用不上。那就让能用的人去用。当然啦,也可以捐出去,但我不想那样。我喜欢开个书屋的感觉。
晓凡说:可那也是钱买来的呀。
江老师和小雪又一同瞪着晓凡。晓凡说:好好,不说钱。
江老师老伴儿突然转过头说:你爸的书,接近准确的数字,应该在一万七千三百五十本左右。除去会议当礼品发的,除去公款给报销的,除去朋友送的,这些大约在一千多本,所以,自己花钱买的应该在一万六千本,四十年左右时间,书价从五六元到六七十元,精装的还要贵些,差不多十倍的价钱,咱们取个中间价,按平均每本三十五元算,那么这些书的花费大约是五十五万元。当然,最近这几年可以网络购书,能打折,可是你爸喜欢去实体店。所以,五十五万是保守的估计。
全家人,除了江老师老伴儿自己,那三个人都惊诧地看着她。小雪捂了嘴巴轻轻说:天哪,这么多钱。
江老师笑着说:你妈可是高级会计师。领教了吧?
江老师老伴儿说:我可不是说钱。你爸这样的人,是靠书撑着的,不读书呢,他也干不了别的。我还说那句话,买书买不穷日子,五十五万,大约平均每年一万多点,四十年这不也过来了?晓凡不是也养得挺好?小雪的爸,是医学教授,我想他的书也买了不少吧?这不把你也养得这么好?
江老师老伴儿看看没人搭她的话,自嘲地说:我不懂哈,我也不知说得对不对,其实呢,谁的日子不是靠书撑着的?我听老辈人说过,书就是道理,就是你前边日子的道理,和后边日子的道理。懂了道理,日子才过得下去。只是呢,有人要多读些,有人少读些是了。
这样的话,听上去虽是朴素无华,可是,却中肯又实在。江老师是历史学家,心里早是上下都通了的,听着老伴儿说的前边的日子和后边的日子的话,心里的感慨便更多些。他轻轻闭眼就能看回到四五十年去,或许更远,那长河中还有些年是烧书的,两千年下来,一千年下来,一百年下来,都有烧书的。还有禁书的。可是书,就如大地里的种子,真是烧不尽又禁不住的。只要有一丝春风,有一缕阳光,就会遍及人间的。晓凡和小雪都是四十出头的人,没经历过这个,但愿他们的日后不再经历。
江老师轻声说:你妈说得是。日子绵绵悠长,有书相伴,人才活得明白。
晓凡和小雪,还不算是个读书人,父亲的话,说白也白,说深又深,两个年轻人似懂非懂的,一时也接不上江老师的话。
四个人一时无语,听窗外那初夏的细雨打着树叶,沙沙地响。
书店也好,书屋也好,先要有个地方。江老师只是向儿子媳妇通报一下,事情并不麻烦他们办,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子,都忙着。
也是巧了,江老师的一个学生小郑,跟江老师读研究生的,父母是有钱人,城里城外都有房子,住着大别墅。一个欠他们账的商家,手上没钱了,便拿了一间房子抵债,房子正是在江老师住的小区临街的一楼,那种叫做“底商”的。原是想着开个小门市,可是小郑的父母都忙着挣大钱,哪里有工夫管这一间小房子?说租出去吧,又怕没人管理,糟蹋了房子,还不够操心的。小郑研究生毕业后,被江老师推荐到一家出版社工作,也忙得晕头,更是不管,房子就还是空着,拿一把大锁锁了。
小郑知道了江老师要开书店的事,一个念头一闪便定格了。跟父母打了个招呼,又特意跑到江老师家里,毕恭毕敬地说了房子的原委,事情便定下来了。一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开个书屋正合适。江老师问起租金,小郑说,老师,您是我的恩师,我不敢说报答您,但您要开书屋,这是功德之事,我正巧有这个便利,跟钱没关系。江老师知道小郑家的底气,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便点头接受了。
这是在和儿子媳妇通报之前的事,就是说,江老师说要开书店的时候,已经把书屋的房子找下了。
当老师有一样好,学生多,学生多办起事来就方便。小郑也不让江老师操心,在手机群里一声招呼,便有人来帮忙,都是江老师的学生,各人有分工。几天的工夫,书屋的房子便粉刷了一遍,地板打了蜡,换了新的玻璃大门,门前还铺了红地毯,门脸上方,也不知哪个有能耐的学生,弄了一大块厚厚的原木牌匾挂着,匾上刻了几个大字:“灯火书屋”——原木是淡栗的底色,字是白色,醒目又素雅,一点儿也不输给左右两旁的店家。书屋的左手,是一间茶店,陈升号普洱茶,老字号的。再往左,是一家便民药店。挨着药店的,是一家眼镜店。书屋的右手,是课外美术班,由两个老师教小孩子画画和书法。再往右,是一家烘焙店,做精致的点心。挨着烘焙店的,是一家孕婴服饰。再就是一家鲜花店。一条小街,整齐干净,说安静呢又有人气,说人气呢又不是闹市。书屋开在这里,是个合适的地方。江老师很是满意。
小郑挑了几个细心的女生,又给发了细布的白手套,脚上套了鞋套,进了江老师的书房,江老师只留了几本珍贵的孤本善本、自己的著作,还有百十本买来没有细读的,其他的全部打包。几个女生用了三天时间,小心地把书放进了几十个大纸箱,又叫了两个干粗活儿的男生,捆扎好后,雇了个搬家公司的小货车,把书拉到了灯火书屋。书屋里早用白茬木打好了几排大书架,用砂纸打磨了,不让刮到书,小郑知道江老师不愿用那种组合的铁架子,既怕伤了书,又看上去冰凉着,没温度。书屋里的设计也很别致,木头书架子没有贴墙,而是在屋子中间排了三排,都是双面的,等于是放了六面书。东西两面的墙壁,贴着墙放了两排单人的座椅,座椅前放个小桌板,每个小桌板上立了个小台灯,每个座椅间都立了个小隔断,阅读的人不会互相影响。东西两面的座椅各九个,南墙窗子旁放了两个,北墙的拐头放了三个,这样,整个书屋的座位是二十三个。南墙的一个角落,挨着大门,放了一张书桌,给值班看店的人坐。北墙的角落,立了个简单的小茶吧,供应咖啡和茶水,免费的。茶是方便冲泡的茶包,咖啡是速溶的。
晓凡和小雪也抽空儿来过两回,看看也帮不上什么忙,扎着两手看热闹。晓凡跟小雪说:老爸这是要干什么?图什么呢?小雪说:这是境界。我说句话你别介意。晓凡说:你说你说,我一俗人,怕什么?小雪说:我们都不如老爸,你一个图字,便是与老爸的差距。晓凡说:嘁,把我说的,真好像我多俗似的。老爸这是老了,退了,找存在感呢,就由着他性子吧,反正也不花钱。小雪说:还说你不俗,越说越俗了。
学生们由小郑指挥着,把书放置到书架上,按类摆好——江老师的书,分了几个大类,存量多的一是哲学、思想类的,一是历史类的,一是文学、艺术类的,这几大类占了六七成,还有些杂类的,宗教、地理、法律、传记,不外乎是社科各项,还有些外文书和工具书。旧书有旧得发黄的,新书有刚买来没几天的,真是古今中外,上下千年。一个书房,就是一个世界——忙活了几天,一万七千多册书便摆放整齐,只待开业了。
开业是开业,可毕竟不是卖书的书店,用不着开业大吉那一套。江老师只觉得门前红毯是唯一的败笔,让把红毯撤了去,只把台阶洒扫干净,也不摆什么花篮条幅,也不放什么音乐,选了个晴朗的早晨,便悄无声息地开门待客了。
请了在读江老师研究生的女学生小郝,坐在书屋里看店,顺带引导着读者找书,也不耽误她读书学业。
门前有人走过。有人扭头张望,脚步没停。有人停下看了看,犹豫着。有人到门口伸头向里看,不进,嘴里自语:哦,是书店啊。那看店的小郝便说:不是书店,是书屋,看书的,请进吧,随便看。有人便进来了,这是第一个读者。
来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干净朴素,举止斯文,围着书架转了一圈后说道:咦?这看上去像是私人藏书啊。接着话音,又进来了一个人,是个比小郝年纪小些的女孩,中学生的样子,取了一本书,坐在窗口便读起来。没两分钟,又进来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手里拉着他的妈妈,那妈妈有点不情愿的样子,嘴里说:这不是儿童书店哦,儿子,出去吧。那先进来的中年男人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递给小男孩说:这个看过吗?小男孩说:老师给讲过,可是我家里没有呀。孩子说着也不管他的妈妈,只顾坐下看了起来。
小郝给江老师打了个电话,这是江老师嘱咐的,第一个读者进书屋的时候,要给江老师打个电话。这还不是一个,是一下子进来三个——对江老师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大玻璃门前,靠窗的地方,立了一个小黑板,上面的粉笔字,是江老师亲手写的:
免费取阅 爱护图书
可以带走 只限一本
归期不限 不必登记
可以转借 说明去向
这是开业的前一天晚上,江老师写下的。江老师写了一辈子板书,相当漂亮。为了醒目,小郝又用彩笔给勾了下边,画了个小图案,旁边写了个大大的“静”。小郝边画边提出疑问:老师,那归期不限,他要是不拿回来呢?
江老师笑着说:不拿回来,就说明他喜欢,那就留着看呗。书就是看的嘛。
小郝又说:那转借,他要是说转借这个人那个人,最后说借丢了,那咋办?我要不要登个记呀?
江老师说:不必。小郝我问你个问题,书,是一个人看有价值呢,还是一百个人看有价值呢?
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小郝像是想明白了什么,点头道:我懂了老师。
书屋开门一个月的时候,来了两位不速之客,给小郝亮了证件,自称是文旅局文化市场稽查队的,来查看书店是否有营业执照,是否有违禁书籍。
稽查员说话的声音有点大,此时书屋里有十来个人在读书,其中一个读者向那两人投来不满的目光。来人围着书架转了两圈,没看出什么名堂。小郝有点紧张,赔着笑脸说:我们这不是书店,是书屋。书都是好书,不可能有违禁的。来人说:那不是都一样?叫法不同吧。小郝心稳了一些,仍笑着说:不一样哦。书屋不卖书,只看书,所以不用执照吧?来人问:看书也不收费?小郝说:不收费。来人又问:那开这个书屋干什么?小郝说:就是读书啊。您二位要是走累了,也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看看书,喝杯茶。来人看到茶吧,又问:喝茶免费?小郝说:是的。另一个问:你开的?小郝说:不是,我哪里有这么多书,是我老师。那人问:你老师是谁?小郝说:××大学,江书河教授。那人又问:房子不是要付租金?小郝说:不用的,是自己的房子。另一个问:你老师自己的?小郝说:不是,别人的。又问:别人是谁?小郝说:是我的一个学长,人家自己家的房子,空着没用。两个稽查员对视了一下,先说话的那个又指着黑板,问道:书还可以拿走一本?小郝说:是的。那人又说:那我今天拿了,明天要是再拿一本呢?小郝笑着说:也可以呀。只是,书是用来读的,读一本书,怎么也要一周两周时间吧,您可以送回来一本再拿一本呀,为什么要连着拿呢?那人去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对小郝晃了晃说:真拿走了?小郝说:可以呀。两个稽查员对视一下,摇了摇头,走了。到门口时,拿书的那个说:这书我会来还的啊,公事公办,拿回去跟领导汇报。小郝指了指黑板说:不急,归期不限哦。另一个突然又进来,拿手机把小黑板拍了个照,两人走了。
一传十,十传百,灯火书屋在附近一带就有点“火”。都说那书屋看书喝茶都免费,从早上坐到晚上也不管你,又可以不登记就把书拿走,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去肯德基看书还要点一杯可乐呢。一个夏天,来的读者越来越多,常常是二十三个座位不够坐,就有站着读的。
把书拿走的人,都是走到门口,把手里的书冲着小郝晃一晃,让她看清是一本书,小郝便点点头。有的人再来的时候,也冲着小郝晃晃手里拿回来的书,意思是书还回来了。小郝也点点头。也有人再来时,说一声:那个,上次那本书,借给我同学了。或者说:是我弟弟在看。小郝也就点点头。其实,谁拿走的,谁还没还回来,她是记不全的。但小郝是个心灵的女孩,知道老师的意思,所以也不去认真追问,任读者自由来往。
有一样不同,灯火书屋,没有网络,带着电脑来是没用的,进来只能读书。
小郝给江老师打电话,说有个读者问,可不可以把灯火书屋发到网上去?江老师回答说:不要发。书屋要安静,不要吵闹,虽是网上,但在网上也是吵闹。江老师又说:这么点儿书,只是给附近的街坊邻居看书图个方便,发到网上没有任何意义。小郝就跟那读者说,千万不要发网上。
小郝又拿了张大白纸,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了:各位读者,您可以用手机拍照或录制视频,但请千万不要上传到网络。请尊重书屋主人的意愿。谢谢。
那个文化稽查员拿走的书,还真是还回来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来了也没亮证件,把书还了,对小郝说:我们领导说了,江教授是著名学者,他开的书屋,自然没问题。还说,这是善举,我们以后要带着电视台来搞活动,宣传一下。小郝忙说:谢谢领导好意哦,可是教授不会同意的,真的,请跟领导说,教授不喜欢宣传。小郝又指了大白纸上自己写的毛笔字说:看看,不让上网的。稽查员说:这是领导的意思,我只负责具体工作。小郝无奈地说:那也得给教授打电话,他不会同意的。稽查员说:现在只是说说,还没上日程呢。到时候再说。稽查员又说:先前那本,是工作需要,今天我以个人名义再借一本啊。小郝点头说:请随意。稽查员绕书架走了一圈,抽出一本《古希腊文明的光芒》。小郝说:对历史感兴趣?稽查员说:读着玩儿。那个,这书是上下两册,下册,能不能帮我先放起来?我怕有人借走了,一时找不到,我这是不情之请啊。小郝想了想,走到书架前,抽出下册,交给稽查员说:给你破个例,都拿走吧。稽查员倒不好意思起来说:这行吗?小郝说:拿着吧,你虽然说读着玩儿,但是不会有人读这本书玩儿的,可见是感兴趣。难得。稽查员说:你还挺懂的,谢谢啊。对了,你是?小郝说:我是江教授的研究生。稽查员换了脸色道:哦,失敬了。请多指教。小郝说:哪里,不敢哟。我是学生。稽查员说:都是学生过来的,我学法律的,研究生毕业考了公务员,刚分在文旅局工作。小郝说:那还是请你多指教。稽查员说:我也不敢。互相学习。
小郝把稽查员送出书屋,两人在门前道别。稽查员是个高个子青年,不敢说帅,但长得顺溜,穿一身清爽的夏装,白T恤,米色裤子。许是机关工作的缘故,脸上带了些微的老成。小郝是个身材小巧的姑娘,面容是那种不动声色的好看。中短发,戴一副白色框的眼镜。也是一身清爽的夏装,淡蓝底碎白花的收腰小衬衣,纯白色过膝长裙,黑色细条半高跟凉鞋。
晚夏午后的阳光已不那么热辣,也不耀眼,带了些向秋天挨过去的柔和。这样的日光里,站着这样两个青年,他们的头上,是被同样的日光沐浴着的“灯火书屋”的牌子,远看去,就是这小街上的一道风景,让人舒服、养眼,又赞叹。
一个夏天,书屋每天都不断人,上至白发老者,下至六七岁的娃娃,有人坐大半天,有人匆匆来去,有人带书走,有人不带书走。江老师也不是每天去书屋,赶上小郝有什么事的时候,江老师便去顶班。
江老师顶班的时候,要在书屋里脚步轻轻地转一转,一是看看架子上缺了哪些书,二是看看每人都在读什么书,也许会轻声地告诉那读者,在哪个架子上还有他可能感兴趣的书。也有认识江老师的,知道是教授,拿了他的著作来请他签名。江老师也不推辞,签了自己名字,然后轻声地谢读者。那读者惊喜着说:呀,是我要说谢呢。江老师说:谢谢你买我的书啊。
江老师本以为自己的著作偏生涩,不好读,再一层,也是不愿意张扬自己,便没有在书屋里摆自己的书。给读者签了名字后,便想,这也没什么,书就是给人读的嘛,谁的书不是都一样?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挑那相对通俗些的,拿了两本,摆到书屋的架子上。江老师没说什么,但小郝却留意了,过了些天,还真是有人拿走了江老师的书,而且也是好多天没还回来的。小郝记得那个人,但也不动声色,不跟他要。
夏天很快过去,天气说着就凉快了。待你留意的时候,立秋早是不知哪天就过去了,来书屋的读者,已经要求小郝把空调关掉了。小郝也给自己加了件薄毛衫。小郝到底细心些,她想到一件事,在北方城市,在深秋和初冬的时候,就是在供暖给气之前这段时间,屋子里是很冷的,可能需要加两台电热器。她没有麻烦江老师,而是给学长小郑打了电话,小郑匆匆来了一趟,在书屋里感受了一下温度,他到底懂些,知道安电热器不是那么简单,书屋又是个易燃的场所,消防部门知道了是要监管的。他买了两台大功率的电热器,尽量远离书架,挨着两边的墙放了,又嘱咐小郝小心着,关门的时候要记得关掉电热器。
因书屋不是自己家里,而是在大街上,所以还是被关注了。即便不是经营场所,工商税务文化稽查都管不着,但是消防是能管到的。
一个晴朗的秋日,消防部门挨家排查,从隔壁的药店出来,到了灯火书屋,正赶上两台电热器都开着,虽是都开着中档,但消防员还是说不安全,这满屋子书感觉是随时都能点着。责令关了,还要没收电热器。同来的社区主任说了好话,小郝也做了保证,事情算是罢了。
但是冷的问题又来了。江老师也到书屋坐了一下午,感受了一下。临近黄昏的时候,小郑来了,小郑先和江老师行了礼,然后招呼小郝,帮着他去车里抱出了一堆新买的毛毯,有二十多条。小郑说:毯子就放在椅子上,来的读者,看书的时候,可以搭在身上和腿上。江老师说:办法是好办法,但是你又破费。小郑说:没几个钱,我爹妈赞助的。他们挣那么多钱,给书屋做点贡献吧。过几天供暖就好了,采暖费我已经交过了。
师生三个围着书架转了几圈,两个学生都不怎么敢说话,只听江老师慢悠悠地介绍自己的藏书。江老师看到什么说什么,东拉西扯,看似无心,但张嘴都是学问,两个学生贪心地听,享受这个难得的时刻。
江老师声音虽轻,但还是有几个读者慢慢地跟了上来,跟在后边听。江老师看到了,忙说:哎哟,罢了罢了,影响人家读书了。
几个读者忙说:江老师再讲讲吧,我们愿意听呢。
江老师指了指身上穿的薄羽绒衣说:不讲了不讲了,老了,讲不好啦。屋子里太冷了,你们穿的少,把书拿回家去读吧。
三个人来到屋外,站在台阶上,看秋风吹着落叶往地上飘,看马路上来往的车辆轧着叶子驶过去,看行色匆匆的人和悠然自得的人从眼前走过。
小郝轻声问小郑道:学长,你注意到书架了吗?小郑问:注意什么?小郝说:书已经开始少了。小郑说:哦,你这一说我倒是注意到了,是少了。有多少呢?小郝说:我大致数了下,大约三千多本吧。小郑惊道:那么多?是没还回来吗?小郝说:总是没还的比还的少吧。有的人可能也不想还了吧。你看老师四个版本的《红楼梦》,二十多册,一本都不剩了。摆明了是不还了。还有两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早拿光了。虽然明白老师的意思吧,但还是有点心疼。小郑说:看看你,心胸小了不是?小郝点头说:学长批评得是。小郑看着江老师的背影,轻声对小郝说:这么拿起来,老师这两万来本书,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两三步远的距离,两个学生的对话,江老师都听到了。江老师回过头说:小郝,明年的夏天,你就毕业了。你得再找一个师妹,来帮忙看这个书屋了。小郝摇头说:老师,我毕业了还接着看。江老师笑说:那哪行,你还得工作呢。是舍不得这个书屋吗?小郝说:都舍不得,更舍不得您。江老师笑说:哈哟,我有一天会走的,这个书屋早晚也会空的。
小郑说:老师,您不会走,书也都还在。他用手画了一个大圈子——在那么多读者的手里。
江老师拂了拂灰白的头发,长舒了口气说:啊呀,此生足矣,足矣呀——
小郑和小郝一边一个,靠近了他们的老师,紧挨着他,他们的眼睛已是湿了。
秋阳夕照,“灯火书屋”的几个大字,立体、饱满、美观、大方,不时有路人对那牌子望上一眼,有人过去了,有人进了书屋。
阅读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