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1。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2。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3”,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4。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5。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6;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7。”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8,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9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10?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11。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12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1礼教治政云尔:礼乐政教等等。
2大体归然而已:大体上归到礼乐政教方面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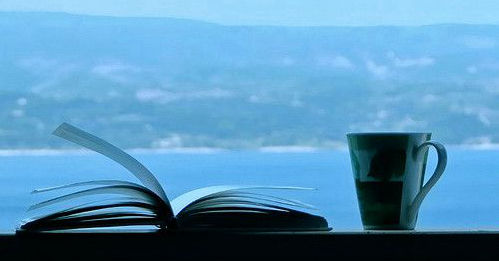
3辞之不可以已也:光有文辞是不行的。
4不如是其已也:不是这样的。
5欲其自得之也:自己在心中有所得。
6资之深:所取用的资本很充足。
7取诸左右逢其原:左右逢源,事事能顺。
8非直施于文而已:并不是只用来写文章。
9辞:文词。
10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要是没有雕饰刻画,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11勿先之,其可也:只有不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12阿:恭维、逢迎。
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文”与“辞”的关系,我们知道其实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大文人学者提到过,首先孔老夫子就曾提到过这两者的关系,而到了唐朝的韩愈那里,再到了宋朝的欧阳修那里,都阐述了“道”的核心原则,文应该是为道服务的,这就是“文以载道”的观点,不过不同之处在于,韩愈和欧阳修所说的“道”更多地趋向于儒家的圣人之道,也就是天地间的真理,而王安石这里说的“有补于世”,其实更多地侧重于“术”的层面,这是后来一直沿着的道路,侧重于“术”而忽略于“道”,这就使得文章缺乏一种深度和厚度,所以这也就是韩愈、欧阳修与王安石文章的一个小区别。而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了。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
阅读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