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过一个关于手绢的故事,那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剧中的黑人统帅奥赛罗曾送给他最疼爱的女人苔丝德蒙娜一块手绢,做为二人的定情信物;却因奥赛罗的愚顽与固执,轻信了身边的小人伊阿古的谗言,误以为苔丝德蒙娜与自己手下的爱将有染,而那手绢最终成了苔丝德蒙娜绝命的“罪证”。虽然那“有染之说”纯系子虚乌有,虽然苔丝德蒙娜是纯洁的、无辜的,但纯洁感化得了奥赛罗的愚顽与固执吗!无辜救得了苔丝德蒙娜的命吗!当奥赛罗抱着刚刚被自己掐死的苔丝德蒙娜的时候,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一切已无法挽救——他被小人戏弄了。我一度不解,难道那手绢上会有什么不祥……
懵懂中,想起了朋友讲给我的又一段关于手绢的故事,一段感人又令人惋惜的故事。一方绿色的、绣着一颗心型图案的手绢,那是一个俊朗男人送给一个中年靓丽女性的方手绢,成了他和她之间相识与沟通的一座“鹊桥”。是一次不期而遇的偶然出行,两个陌路之人,从躲躲闪闪的最初对视,到断断续续的交谈,到相见恨晚的热聊,俨然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朋友。当然,后来的同行便成了二人深入交往的催化剂。这样的不期而遇,让她情动不已,让他如获至宝。同行结束,各奔他方的时候,两人面对面,脉脉含情,难舍难分。他从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小手提袋,递到她的面前,“做个纪念吧!”泪眼模糊的她接受了他的礼物。“打开看看!”乖乖地,她打开了手提袋,一方绿色的方手绢呈在眼前。她捧着那方绿色的手绢,想起了他选购时的情境,心里涌起难以言喻的激动:原来你是在为我准备礼物啊!她凝视着他,下意识地把那方手绢紧紧贴在胸前,一股幸福感让她长时间地闭上了眼睛,任由泪水酣畅地流淌。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不舍地分别了。从那以后,这方绿手绢便与她形影不离,想起他来,就掏出来嗅一嗅,吻一吻,那上面仿佛还残留着他的味道,仿佛还闪动着他们一路同行的点点滴滴。自那以后,绿手绢便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爱。在她和它之间,还曾发生过一段失而复得的小故事:那是送她手绢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带着一只小包包,里面装着那方手绢,和女儿一道去参加朋友的聚会。聚会结束得很晚,连末班公交也收车了,她和女儿只好“打的”回住处。当她下车时发现随身携带的小包不见了,她马上催促司机:“快,刚才的那家酒店!”女儿不解,责怪母亲:“什么事还值得再‘打的’回去一趟?”她并不解释,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司机。“的士”发了疯似地在大街上疾驰,她仍然嫌慢,仍然不停地催促着“快!快!”车到酒店,她连车钱也没顾得给就冲进酒店去找那个服务员。她拉着服务员的手急急地问:“刚才……707包间,一个包包,紫红色的,见到了吗?”当她听说那个小包包没丢时,一边连声道谢一边追问:“小包在哪儿……在哪儿?”服务员指着大堂经理的办公桌,“看见了吗?”办公桌上,那个最熟悉的紫红色的女式手包就放在电话机旁,“正是,正是!”她两眼充满了惊喜,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个紫红色的真皮包包,急急地打开拉链,掏出了一块绿色的手绢,慢慢送到唇边,轻轻地吻着,一遍遍地自语:“我的上帝啊,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付了车钱的女儿看着母亲激动成这副样子,哭笑不得,“妈,你今天是怎么了?一方绿手绢,你说值吗?!”渐渐从焦虑与兴奋中平静下来的她点着女儿的额头,认真地只说了一句话:“傻孩子,你不知道啊!” 是啊,女儿怎么会知道那是她的心仪之人送给她的信物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上面饱含着的是她对心仪之人的牵挂和思念呢!
女儿被这故事震撼了,明白了一方小小的手绢在母亲心中的位置,更明白了那方小小的手绢的失而复得竟让母亲如此忘情的缘由;这就是一种渴望、一种期待,这就叫爱吧。女儿猛地想起了自打自己记事起耳闻目睹到的家庭生活,想起了从小就听惯了的父母的吵架声,想起了记忆中母亲的生活,那里缺少倾心的呵护,缺少真挚的疼爱,更缺少包容和理解。一个文化人为了自己多磨的家庭,违心地嫁给了一个缺情少爱的男人。
母亲的婚姻,是在被对方强烈追求而又迟疑不定的时候,家里给促成的。因为,母亲大学毕业已经26岁了,在那个年代,已是标准的大龄女青年,母亲虽没有强烈的嫁人欲望,但家里着急。于是,与比自己大4岁一个同班同学相处了仅仅几个月,还不知道什么叫恋爱时,就成了人家的媳妇。那婚姻里根本没有爱,只是一种莫名的驱使。母亲虽有些违心,却认了,甚至还时时想调理出爱的滋味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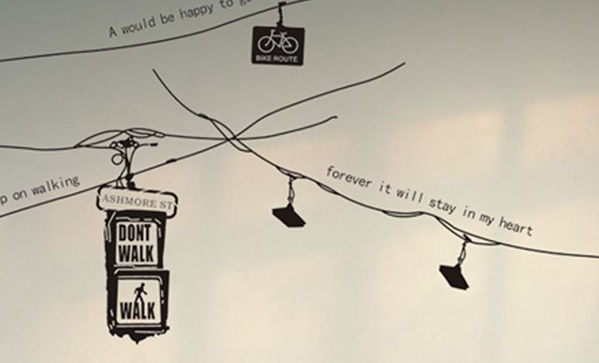
女儿清楚记得,父亲虽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却酗酒成性,常常深更半夜喝得醉醺醺的回家,而且进门就骂人;甚至有时吐得床上床下满屋子都是。吐完了,没事人一样的父亲倒头便睡。那呛人的腐臭叫人作呕,早没了睡意的母亲每次都要忍气吞声地收拾,等都洗涮完毕,天也快亮了。
女儿还记得,父亲是个感情不专一的男人,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说父亲在外面有人了。母亲怕别人笑话,一直忍着;心里苦苦的,却从没有泪。母亲知道眼泪感化不了铁石心肠的父亲;从那时开始,母亲便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女儿身上,以此来弥补空落的内心。
女儿更记得,父亲是一个极没教养又脾气顶臭的人,稍不如意,就拿母亲出气,甚至拿自己出气;拳打脚踢,无所不用。有一次把母亲从屋里打到屋外,又把母亲踹得滚楼梯。家暴生生地把母女俩逼出了家门,她们无法面对这种粗暴,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决意带着女儿远走异乡了。
女儿忘不了,父亲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与母亲分居后,他带了女研究生,却没有想到日久生情,竟使比他小20几岁的对方有了身孕。毫无羞愧的父亲找到母亲,恳求母亲与他办离婚手续。自那以后,父亲便不再与她们有联系了。
女儿同情自己的母亲,在自己成人之后曾多次告诉母亲,跟这样的男人分手就对了,有这样的父亲自己都觉得丢人。而每逢这时,母亲总是无奈地摇摇头。
又是一次出行,是母亲为了去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去见那个送她绿手绢的人。在大西北的黄河之滨,母亲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那种兴奋自然难以言喻。7天的欢聚,母亲得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最爱;只是时间太无情,匆匆的欢聚,刚刚调理出幸福的滋味来却又要匆匆分别了。
离别之时,她和“哥哥”,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两只拉着的手越拉越紧,两双噙满泪水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没有话,只有抽泣。开车的汽笛声响了,这往常听惯了的声音此刻却像一阵呜咽;母亲一下子放出了哭声,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过脸颊;“哥哥”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边摇着头一边重复着一个字:“别……别……”列车启动了,紧拉着的手被无情地扯开。母亲的哭声更大,她伸着双手,使劲地伸着,朝着“哥哥”;她顾不了什么气质、什么疑惑的目光,只是任由自己宣泄着对“哥哥”的眷恋与难舍,“哥哥……”母亲不停地拍打着车窗玻璃,只是哭。西行,让母亲圆了一份孕育许久、期盼许久的情缘,让母亲在人到中年之时找到了真正爱慕的人,也得到了来自对方的真诚的回报。虽然只有短短的7天,但母亲却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7天里,母亲一直兴奋着,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绕着她深爱着的“哥哥”,飞啊,叫啊,仿佛换了一个人,话语格外多、格外甜,听得“哥哥”一个劲地傻笑,却一句话也没有;7天里,母亲的脸上始终堆满笑容,仿佛要将心底的愉悦昭告给天下所有懂爱的人。当西行行将结束的时候,这只快乐的“小鸟”累了,不飞了,不叫了;眼睛直直的,脸色阴阴的……她几次悄悄对自己说:“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刚刚开始,却要结束了。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一想到就要和“哥哥”分开了,我说什么也乐不起来,我觉得这些天里“哥哥”对我的好都模糊了,留给我的只有这最后的留恋。我不敢去想明天,太残酷了……”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上车前“哥哥”送她的小礼物,从挎包里翻出了那个方盒,打开一看,一方蓝色的手绢;纯纯的高原蓝,上面是几片洁白的云,下面两只小羊拥在一起。好辽远又温馨的情景。她又在挎包里翻出了那个紫红色的手包,拉开拉链,掏出了那方绿色的手绢。两方手绢,一蓝一绿;她明白了:这就是“哥哥”的家乡啊,他把他的家乡装在手绢里,送给了她……她,手捧着两方手绢,捂住了脸,轻轻的抽泣声透过手绢,传得很远……她与他分别了,那两方手绢,成了最亲的见证;那上面,有相识的信息,有告别的泪水。
女儿终于明白了,母亲需要爱,渴望爱;在没有爱的家中,她太苦了。女儿更理解了,母亲对当初那方绿手绢的用心与动情,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收获。可是,如今,母亲与那位送绿手绢又送蓝手绢的叔叔怎样了呢?母亲只是更多地说过他与那位叔叔的那7天重逢,讲过那7天里最难忘的真实体味;觉得母亲很享受,那是母亲的一次真心的心动。那以后,便再没听母亲说起过她的那段艳遇,只是告诉她那位叔叔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而那两方手绢一直藏在母亲的那个紫红色的手包里。
没有必要去查考故事的真实性,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曾几次听说的关于送女人手绢的提示:千万别送女人手绢啊,人说送女人手绢结局不好的。奥赛罗送手绢给苔丝德蒙娜,成就了一代经典;那位“哥哥”两次送手绢给她,却只留下了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如今,手绢,不,应该叫方巾了,好像与人们的生活不那么亲近了,渐渐远了,那方形的织物仿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市场上还有出售,但方巾与情感已经再难续写新的情缘了……
阅读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