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珠玑古巷
在岭南,保存完好的唐宋古遗迹不是很多。如果有,那可称之为稀世之宝。在南雄,除了三影塔,还有珠玑古巷。这是广东省仅存的、保存完好的宋代古道。虽然名为巷,实是小街。不要说是广东,就全国而言,宋代保存到现在的古街,也没有几处。所以,当我来到珠玑巷,我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我一遍又一遍在珠玑巷行走,恍若置身时空隧道。你会看见那些从大庾岭下来的迁客、流民、贬官等等源源不断会聚到这条岭南狭小的官道。他们满脸疲惫,摩肩接踵,推搡拥挤着。甚至,你还会看见韩愈、宋之问、苏东坡、汤显祖等面色忧伤踉踉跄跄向南走去。这种情形很容易给初来岭南的人们一种错觉,岭南原来也是这样的热闹啊,哪里还有什么蛮烟瘴雨大蟒鳄鱼?
他们哪里会想到,岭南,正在悄悄地给这些满脸疑惑的中原人以颜色。天空的烈日像火球一样炙烤大地。强烈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在身上。渐渐地,他们身上的衣衫,全被汗水湿透。
我生活了将近30年的扬州,有一条著名的东关街,扬州八怪中金农、板桥都曾在此街流连过。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是当年盐商、官宦、画师、墨客雅集之地。我曾在东关街的最西端,与国庆路的交会处,面向北,开了一家艺兰坊书肆。每日行走于此,就感觉行走在历史的时空里。后来,扬州人明白了这条街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彻底的翻修,终于成为扬州旅游的又一绝佳去处。其实,与南雄的珠玑巷相比,那只是一条明清古道。
如果从中原南来,欲过大庾岭,那么在过岭之前,定然会在大庾县稍作休整。然后再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之后,便是神秘未知的异域他乡。南雄县的珠玑巷,成为中原人千里迢迢来到岭南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他们在这里会逗留一段时间,面对连天的古榕婆娑的棕榈和顶天立地的木棉,他们思忖着该如何去穿越蛮烟瘴雨,如何从这里走向孔雀鳄鱼大蟒栖息的山岭。
珠玑巷至今有千年的历史。完全是中国古巷道的活化石了。其得名于唐敬宗年间,据明末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云:珠玑巷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祖,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予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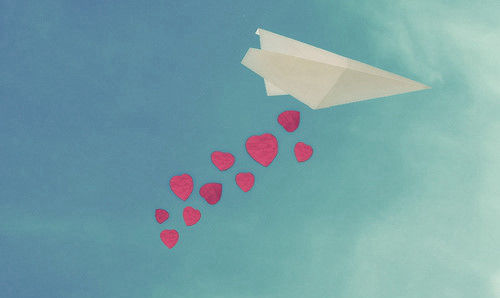
现今的珠玑巷中,有张兴故居。生活在珠玑巷的很多百姓,对那位唐敬宗可谓感恩不尽,让这条千年古巷带来繁荣与福祉。只是,唐敬宗李湛是个短命皇帝。在位仅3年,年仅18岁,即被人合谋杀死于内室。为避敬宗庙谥,敬宗巷便改称珠玑巷,沿用至今。
珠玑巷,原是沙水镇的一条小巷,位于沙水河西侧。两广总督阮元编的《广东通志》云:珠玑巷在沙水寺前。原来珠玑巷大体位于沙水镇南端,即从古巷门楼起,向北,经石塔到石桥,这一段约长二百米。再向北,则是其他巷、里、坊。如今之珠玑楼,过去并不属珠玑巷。据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楼碑记载(此石碑现仍镶于珠玑楼),珠玑楼原为沙水镇翔凤坊之楼,早塌,乾隆十二年重建时,才题名为珠玑楼。
明陆深撰《南迁记》中记述,沙水镇还有儒林里,沙水塘等旧址。但是后来,随着南迁的人越来越多,珠玑巷的名声日益显赫,与山西的大槐树一样,成为岭南拓荒者的精神故里。来珠玑巷寻根问祖的人越来越多,珠玑巷的名声响了,沙水镇的里、巷、坊,都像翔凤坊那样,逐渐被珠玑这个名称所替代。原来的沙水镇没人知晓,一说珠玑巷,则无人不知。历代行政区域,却一直沿用沙水这个名称。宋嘉定中称沙水驿,后又改沙角巡检司,清名沙水塘,民国为沙水圩。今名珠玑镇,辖110多个自然村,3万余人口。
珠玑巷离南雄城九公里,该巷南起驷马桥,北至凤凰桥,全长一点五公里,宽约三米。其古朴风貌犹存。珠玑巷有三街四巷,即珠玑街、棋盘街、马仔街;洙泗巷、黄茅巷、铁炉巷、腊巷。现存古迹,主要有古巷、古楼、古塔等。珠玑巷的南端为古巷门楼,砖石结构,中有拱门宽约3米,拱门正上方雕有珠玑古巷四字碑刻一块,右上方镶有民国十六年碑刻一块,题为祖宗故居。
【二】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每当我读到这个词,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滋味。衣冠者,是相对于岭南的百越人而言,代表了中原先进的文化。那应该是文明之地啊,怎么还会发生战乱、割据、民不聊生?每当中原发生战乱或天灾人祸,大量中原人就会纷纷向南迁徙。这些南迁的人,在兵荒马乱之中,扶老携幼,历尽艰险,越过大庾岭,来到百越之地。
唐末战乱、农民起义、五代纷扰。千百年间中原少有安定的时期。战乱频仍,而粤北岭南却像个避风港。这些人从中原南下,说得好听,是移民。实际上呢,是难民。历史上的数次大规模的迁徙中,北宋、南宋之交,大批官宦士子南下,来到珠玑巷,惊魂甫定。一时间,小小的岭南小镇挤满了南下的人群。经元、明陆续不断有不同家族迁入珠玑巷,遍及附近的许多村落。因为珠玑巷位于南雄盆地中部,土地比较肥沃,有沙水河灌溉,宜农宜牧,又居交通要冲,商业相当繁荣,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一波又一波的南迁之人中,有很多就这样在珠玑巷停顿下来,在此安居乐业。
但是,更多的人却把目光投向远处。他们向北江下游、西江中游、珠江三角洲辗转迁徙。他们具体的线路,大致是:离开珠玑巷后,下浈水,乘船或乘竹筏而行,经始兴、曲江,流入北江,一路漂流。到达清远邑江口一带,开始上岸,或向接连北江的支流水道疏散;还有一些移民则继续南下,经三水、芦苞,入古南海,进入新会、中山,再流向其他地方。途中历尽艰险,到了目的地后,或插入当地乡村,或在荒野地开辟家园,都在顽强地生产,顽强地生活,为当地的开发起到了突出作用。
据史料称,自唐、宋、元三朝数百年间,由中原南下珠玑巷的大规模迁徙行动有三次,较小规模的也有一百多次,从北移来而后,经珠玑巷,又南迁珠江三角洲、港澳,以至美国、东南亚等海外各地。
这些南来之人,即为后世之人一直称道的客家人。他们南迁的同时,也给岭南当地的土著带来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产生了许多名人、学士,使岭南文化也有了崭新的一章。
【三】摩肩接踵
珠玑巷每天要接待如此众多的迁客、商旅、流民、贩夫走卒。一时间满街茶楼酒肆,客栈饭馆,生意好不兴隆。小小的珠玑镇,真有些应接不暇。除了南迁的中原人驻扎在珠玑巷,还有一群人,他们要北上。那就是运送铜与盐的挑夫。
岭南的韶州(今广东韶关)岑水场,在古代是个很大的铜矿。宋皇祐年间,在此采铜,年收购铜五六百万斤,北运铸币。煦宁年间,在韶州设永通监铸币,年产一百多万缗(古代计量单位。如钱十缗,即十串铜钱,一般每串一千文),约重五百余万斤。这些铜币北运,至少要挑夫十万人次。
还有盐运。北宋时即有大批广盐运入江西,赣南上百万人口的食盐,都由广东沿海北运供应。《南雄州志》载,一年约有五百万斤广盐,由沿海船运至南雄,再由陆路,经珠玑巷,北过大庾岭,运抵赣南。这么多的盐,所需挑夫,也得十万人次以上。
此外,还有其他南来北往的客商,海外使者,无法计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一书记述,明神宗二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一行越过大庾岭时,看到客商来往的情形: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

黄公辅,明万历年间进士,官御史,广东新会人。天启二年(1662年)晋升南京山西道监察御史。天启四年奉旨巡按下江,处事公正严明,深受百姓爱戴。次年太监魏忠贤专权,捕杀东林党人,黄上奏控告魏二十四条大罪,结果被撤职回乡,闲居九年。回乡途中,路过珠玑巷,他写下了一首诗,描写了珠玑巷当时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繁华景象:
过沙水珠玑村(明·黄公辅)
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
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
已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知。
遥忆先人曾赋此,百年泰运又还期。
清代同治年间的茂名举人杨庭桂,在《南还日记》里描写了当时珠玑巷,仍然是一片繁忙拥挤的景象:古道上行人熙来攘往,集市上人声喧哗鼎沸,比看唱戏的人还多,走起路来如蚂蚁一般迟缓。
这样的繁荣,一直延续到粤汉铁路修筑之后,才渐渐衰退。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海运的发展,特别是粤汉铁路、韶赣公路开通之后,南北交通状况有很大变化,南雄至大庾的古道为公路、铁路、海运所代替,珠玑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地理优势,逐步衰落下去,由繁荣的商业圩镇变成为以耕种为主的农村。但是,珠玑巷前后繁荣昌盛了1000多年,它是岭南文化的脐带。时过境迁,很多千年的遗迹已无存在,可我们能在这条古巷道上漫步。那石桥旁,还有一棵千年古榕,默默注视着世代的沧桑变迁。
阅读感言